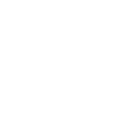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新进展 章节述评

刘军 教授
l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科教授,主任医师,博士生导师,神经变性病与认知障碍专科主任
l 中国康复医学会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,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神经内科分会主任委员,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主任委员,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学组组长
目前全球痴呆患者超过5000万,预计到2050年,患者总数将达到1.5亿,其中阿尔茨海默病(AD)患者占到60%-70%[1],是21世纪的主要健康挑战之一。AD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病变,病程漫长且处于不断进展中,早预防、早治疗对该病至关重要。但现实是AD的诊疗面临重重挑战。AD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,这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寻找有效治疗靶点和诊断性生物标志物的难度。此外,既往常用治疗药物仅能改善症状不能治愈AD,这也是治疗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。虽然面临如此多的挑战,但AD领域专家一直在努力探索,不断从基础机制、生物标志物、药物研发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,希冀为AD诊疗添砖加瓦。那么目前国际上AD药物的研发现状如何?AD的发病机制是否有新的进展?有无新型生物标志物可用于AD诊疗的预测?本期三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论述和研究。
在药物研发进展方面,2021年5月,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联合健康科学学院脑健康系的Jeffrey Cummings教授在国际知名杂志Alzheimer’s & Dementia发表文章“Alzheimer’s disease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: 2021”(《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管线:2021年》),从AD的在研药物及药物靶点等方面汇总了药物研发的新进展[2]。文中提及,截至到2021年1月,有152项关于AD疗法的临床试验,涉及126种药物,大多数药物旨在聚焦AD的发病机制来实现疾病修饰,主要包括淀粉样蛋白(Aβ)、Tau蛋白、炎症/感染、氧化应激、代谢和生物能量、血管因子、突触可塑性/神经保护和脑-肠轴等靶点。总的来说,Aβ和tau蛋白、炎症、突触可塑性等仍是目前AD药物研发的主要组成部分,而脑-肠轴、表观遗传等新型靶点在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上同样具有巨大潜力。
基础研究结果是临床应用的前提和钥匙,AD的基础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。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遗传学和基因组科学系Bin Zhang团队于2021年4月在Alzheimer's & Dementia杂志中发表“Integrative metabolomics-genomics approach reveals key metabolic pathways and regulators of Alzheimer’s disease”(《综合代谢组学-基因组学方法揭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代谢通路和调节因子》)一文[3]。为明确AD代谢特征的相关问题,该研究系统分析了AD患者的多组学数据,对1518名受试者的代谢组学分析发现,短链酰基肉碱和中/长链酰基肉碱与AD的临床结局(情景记忆评分和疾病严重程度)显著相关,此外从MCI进展至AD的患者中,中/长链酰基肉碱水平显著升高。综合该研究其他结果提示,低水平的短链酰基肉碱/氨基酸和高水平的中/长链酰基肉碱可能是AD早期高度预测性的诊断性生物标志物,这一研究结果为从代谢角度考虑AD早诊早治提供了新思路。
随着技术的发展,高灵敏度检测技术让检测AD血液标志物的理想照进了现实。同年11月,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临床化学系神经化学实验室的Charlotte E Teunissen在国际知名期刊Lancet Neurology(《柳叶刀•神经病学》)上发表题为“Blood-based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’s disease: towards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”(《阿尔茨海默病的血液生物标志物:走向临床应用》)的综述[4]。综述中提及,得益于新型高灵敏度的检测技术,血液中微量Aβ、磷酸化Tau蛋白(pTau)和神经丝轻链蛋白(NfL)以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(GFAP)已可被检测到。在散发性AD中,血浆Aβ1-42与Aβ1-40比值(即Aβ42/40)与脑脊液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(PET)中Aβ异常具有一致性,同时,血浆中错误折叠的Aβ1-42及Aβ42/40比值降低与认知功能下降和疾病进展相关。随着高敏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影像学的配合,新型标志物将不断涌现,均有助于推动改进当前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开展。
当今社会老龄化进展日益严重,受AD困扰的家庭逐年上涨。目前临床使用的药物仅能改善患者的症状,多数疾病修饰疗法的相关药物仍处于临床试验中,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顺利上市的AD治疗药物并不多。由于AD的发病机制未明且靶点众多,因此对AD病理机制及生物标志物的进一步探究是研发有效药物的基础,同时借助于不断提高的科技实力,有望发现AD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以利于早期诊断并及早预防。
参考文献:
1. Livingston G, Huntley J, Sommerlad A, et al. Dementia prevention, intervention, and care: 2020 report of the Lancet Commission. Lancet. 2020 Aug 8;396(10248):413-446.
2. Cummings J, Lee G, Zhong K, et al. Alzheimer's disease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: 2021. Alzheimers Dement (N Y). 2021 May 25;7(1):e12179.
3. Horgusluoglu E, Neff R, Song WM, et al. Alzheimer's Disease Neuroimaging Initiative (ADNI); Alzheimer Disease Metabolomics Consortium. Integrative metabolomics-genomics approach reveals key metabolic pathways and regulators of Alzheimer's disease. Alzheimers Dement. 2021 Nov 10.
Teunissen CE, Verberk IMW, Thijssen EH, et al. Blood-based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's disease: towards clinical implementation. Lancet Neurol. 2022 Jan;21(1):66-77.